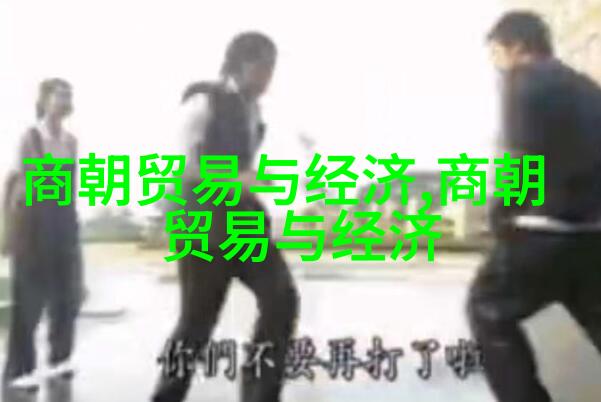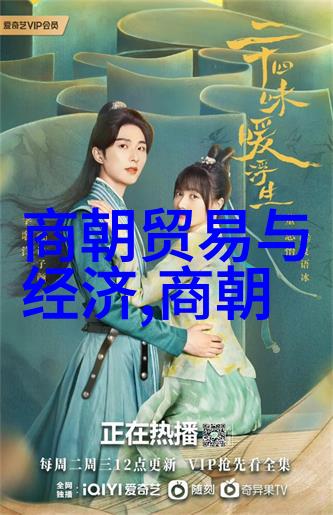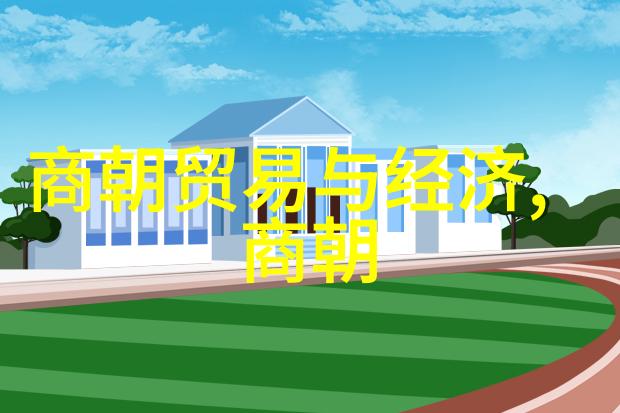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,推广我的新技术到城市污水、炼油废水、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处理工程中。我发现微生物催生了奇妙的反应,就像古代酿酒者一样,让美味饮品诞生。9月3日,我在贵州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了最高科学技术奖,这是20多年科研路程的成果。在台下与颁奖者相隔仅几米,但我的旅程却漫长而艰辛。

跨学科研究让我灵光一闪,我将生物技术应用于环境工程,找到了解决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的方法。我是一个理工男,从中学时代就对哲学和历史感兴趣。从本科到博士后,我跨过化工机械、工程力学、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领域成为首位发酵工程博士后。
1996年,我开始在香港大学进行环境生物技术方向的博士后研究,在导师方汉平教授指导下,从零基础学习环境专业知识,一边看书一边做实验,很快入门。早在80年代,当我注意到工业化进程导致严重环境问题时,就意识到了微生物处理可能成为解决之道。

面对传统脱氮除磷效率低的问题,有没有新的途径?跨学科研究让我找到答案。我相信,将微生物应用于环境治理一定能找到突破口。通过脱氮微生物,我率先成功应用于高氨氮垃圾渗滤液中,看到了神奇效果。
1998年经过1000多个日夜实验分析,我提出了“硝反硝”反应理论,并提出电子计量学,为120余年的国际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。随后的10年里,我不断深入研究并摸索,最终为环保提供了一系列理论基础。此前所学与实践交织,成了我的创新思维来源。

翻越百年的科技高峰,我的跨界背景无意间带来意想不到作用。当我主持研发“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氮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”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,便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
大地才是真正的实验室,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,如周少奇,如果不能直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,那么其价值不够显著。“着眼实际应用”,这是他坚信的事物能够更有生命力。他曾被选派至贵州省环境保护局挂职任局长助理,在那里,他踏遍85个县市区,用他的新技巧促进污水处理建设和产业化应用。这份热情使他成为了西部农村污水处理资源化困扰60多年的重要解决方案提供者之一,也使威宁草海濒危情况得到改善,使得这片天然湖泊再次恢复其碧波荡漾之姿。在这里,每一次小小努力,都像是开启了一扇窗,让自然之美重新回归大地。(张楠 何星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