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突破了生物脱氮研究的国际难题,推动了新技术在城市污水、炼油废水、垃圾渗滤液和农村污水治理工程中的应用。微生物催生了奇妙反应,我则从中解锁了水污染治理的秘密。我以科技之手绘制美丽中国的图景,为此,我得到了贵州省委孙志刚的手中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。我的科研旅程持续20多年,从台下走上颁奖台,只隔几米,却是我心路历程的一部分。

跨学科研究激发了我的灵感。我相信,将生物技术与环境工程相结合,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。我是周少奇,一位贵州科学院副院长。通过跨界思维,我发现了一条创新之路,这也是钱学森先生提倡的人才培养方法之一。在他的回忆中,他认为艺术对科学工作至关重要,它开启了他的创新思维。这就是“跨界”的魅力,对于我而言尤其重要。
作为理工男,从中学时代起,我就对哲学和历史产生兴趣。在本科到博士后期间,我横跨化工机械、工程力学、发酵工程和生物化工等领域,成为首位在我国发酵工程领域获得博士后资格的人。我将研究方向定在环境工程上。1996年,在香港大学进行环境生物技术博士后研究时,我从零开始学习环境污染与治理,很快就融入其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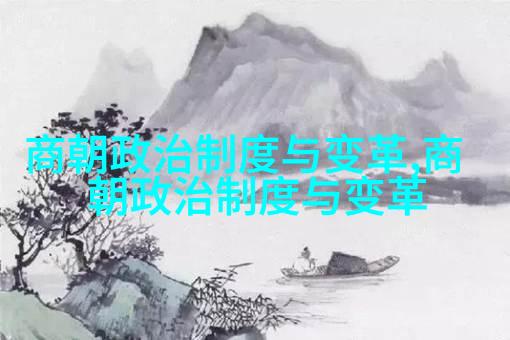
早在80年代,当工业化进程加速时,我注意到了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,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增加,但传统脱氮除磷效率低下需要化学药剂助推。而我,则寻找另一种途径——利用微生物来克服这一难题。当看到微生物如何繁殖并处理有机物质时,便灵光一闪:或许可以用微生物来处理氮磷。
通过实验验证,这个想法成为了现实。在高氨氮垃圾渗滤液中发现硝反硝反应,即有微生物将氨气转换为硝酸盐,然后再转换回氨气。这是一个全新的过程,也是我命名为“硝反硝”的一个自然现象。但当时无法找到相关文献,所以未能及时公布论文。

经过1000余天夜以继日地追踪这个现象,最终提出了电子计量理论,并建立了一系列电子计量方程和系统计量模型,为120余年的国际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。此后的10年里,我不断深入研究,不断摸索,最终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,被誉为“活着最伟大的科学家”。
面对困境,不畏挑战是我不变的情怀。不仅如此,在设计院和企业合作方面也展现出我的积极态度,使理论迅速转变成实际应用,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环保效果。2009年,“含氮有机废水生物脱氮新技术与工程化应用”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;2017年问鼎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,是继宋宝安院士之后第二位获得该荣誉的贵州人。

对于我来说,“大地才是真正的实验室”,因为只有服务于社会的问题才能体现出科研价值。“六化”(即工艺化、设备化、装备化、工程化、产业化、高层次人才培养)是衡量一个科技成果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,而不是只停留于纸张上的知识点。我主张把论文写在大地上,用实践检验真理,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服务于人类发展的大潮流之中。





